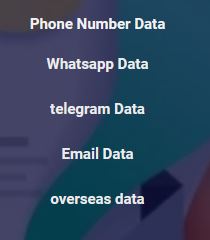上的历史’,让人民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他认为‘历史必须研究不善言辞的大多数人和善言辞的少数人。’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录音机的出现完善了口述历史的做法,使博特金的目标更容易实现。”
换句话说,博特金指示联邦作家以对话的方式进行采访,因为主体间交流建立在共同权威之上,这比口述历史领域中这些核心概念的命名早了几十年。博特金看到了这种采访技巧推动美国生活彻底包容性复兴的潜力,这比科尔在文章中恢复的大众教育和人民历史运动早了几十年。
博特金指示联邦作家以对话的方式进行采访,因为主体间的交流建立在共同的权威 土耳其电报数据库 之上,这比口述历史领域中这些核心概念的命名早了几十年。
博特金深知口述历史的教育和整合功能。他希望让 FWP 实地工作者制作的档案可供“越来越多的公众”使用,“以人们能够理解和使用的形式,将我们从他们身上夺走的、理应属于他们的东西还给他们”,这使他宣称 FWP 的采访计划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教育和社会实验”。虽然这项实验的结果质量参差不齐,但以社会正义为导向的口述历史学家将继续发现博特金令人印象深刻的思想体系是他们工作的特别切题的试金石。为什么?因为博特金的采访方法和理论非常重视人际关系。博特金珍视有意义的接触——用波泰利的话来说就是“相互观察”——不仅是成功采访的基础,也是健康民主的基础。
在 FWP 任职后的几年里,博特金完善了这一理念,他详细阐述了一种面向公众的研究实践,他称之为“应用民俗”。博特金广泛使用这个术语,“指将民俗用于超越其本身的某种目的……进入社会或文学史、教育、娱乐或艺术领域。”他认为应用民俗的基本动力是“庆祝我们的‘共同性’——我们所有人中的‘每个’和我们每个人中的‘全部’……文化群体或层次之间、民间和民俗学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博特金预见了当代历史对话工作的最高目标,他写道:“应用民俗的最终目标是恢复美国人生活中的社区意识——一种沿着相似但不同的路线思考、感受和行动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今天正濒临消失。因此,应用民俗超越了文化历史,进入了文化战略。”
在我最近担任华盛顿口述历史合作项目培训师的工作中,我经常把博特金当作我的个人导师。我鼓励我的采访者在采访中做自己;放松控制对话的冲动,而是像博特金教导他的联邦作家那样,遵循“想法和记忆的自然联想”;并练习将他们的叙述者塑造成他们社区、学校和移民历史的宝贵见证人。我这样做是为了促进联邦作家项目在全国范围内追求的目标——“跨地区综合”——在我们国家首都高度多元化且仍然过于隔离的范围内。
特色图片来源:“联邦作家计划在动物园里展示谁是谁”图片来源不详,通过Wikimedia Commons
- Board index
- All times are UTC
- Delete cookies
- Contact 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