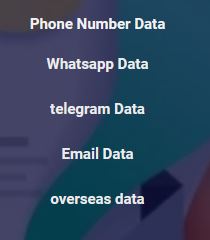事实是,全面和坚定地遵守国际义务的原则——我们的法院从 2007 年“双重”裁决中的第一项开始就告诉我们——可能会与另一项被证明适合为宪法规定的资产提供保护的原则进行平衡;如果后者被认为优先于源自国际法(或超国家法)的规定,那么仅凭这个原因,经营者就不再承担第 31 条要求其承担的义务。 117,I c.,谴责与公约不符的国内法的无效性。简而言之,权利、为整个权的作用是作为宪法 委内瑞拉电报号码数据 条款的附属物的部分)和我们的法院(也许,以更大的决心和精确性)教给我们的教训,特别是在第 n 句中。 2009 年第 317 号,并且在我看来,发送的内容更加具有表现力。 n. 2011 年第 113 号。如果不是因为需要将权利的保护点(实质性保护,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设得更高,那么还能以什么名义强迫法律体系的最高原则,例如法律的确定性,而既判力的本质目的就是保护法律的确定性,而将其置于次要地位呢?
因此,为了满足权利的确定性,即考虑到所有因素,即权利的有效保护、客观的环境条件,法律的确定性似乎必须退居一旁。
事实上,即使在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背后,也存在着构建方法论上的缺陷,只要参考自由宪政主义的原始(但仍然非常有效)理由,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因为——正如十八世纪末的法国革命者所教导的那样——“宪法”的唯一可能含义是在承认基本权利的法律体系中存在并具体化的含义,并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即为了有效地保护这些权利),才建立了权力分立。
- Board index
- All times are UTC
- Delete cookies
- Contact us